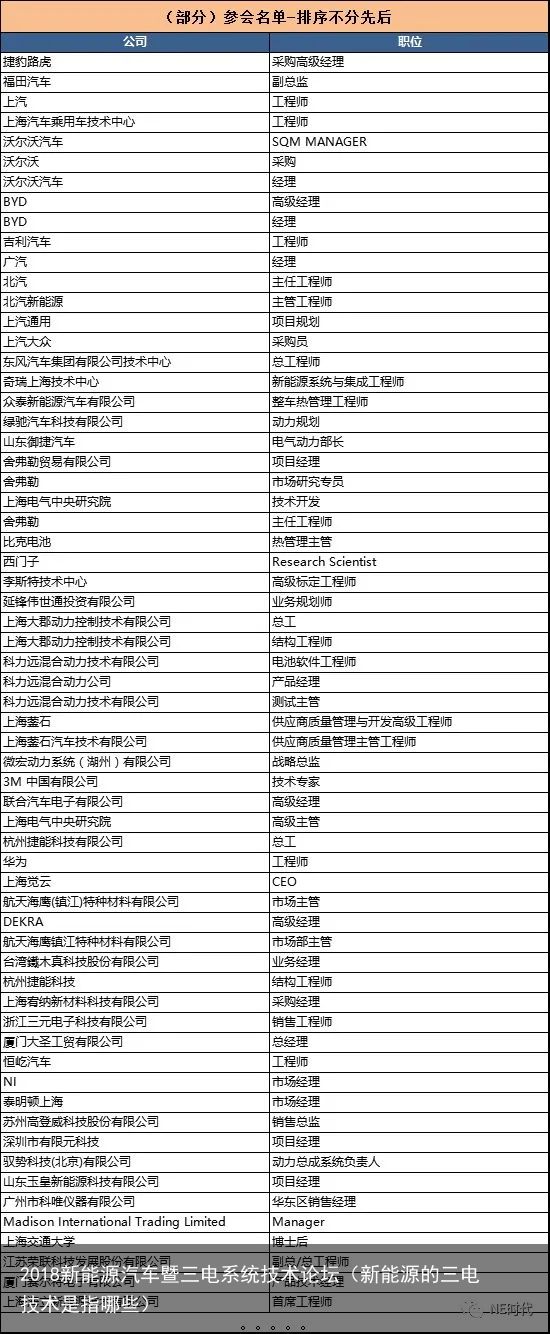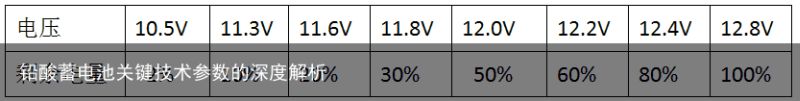一个六六届老高三毕业生的足迹(27) 新同学(高三毕业回顾作文)
27 新同学
我们男生的宿舍,是个新盖的二层楼,宽敞的门厅右手是楼梯。楼梯的上面对着二楼大厅,上楼后穿过大厅一直往前走,对面楼道两边就是宿舍。其中的三间就住着我们班的同学,每间上下铺共住八个人。我住在第一间门里边的一个上铺,两个上海男知青嘉骏和张荣是我的舍友。
开始的两天楼道里乱哄哄的,不光是行李,有人把箱子柜子都搬来了。我就把亲手做的黄菠萝箱子也运来了。我单知道火车站托运大衣柜,包装时一定要把镜子露出来,就忘了装着许多书的箱子,面对铲车也很脆弱。我把箱子外面裹了一层棉被,司机可能当成被摞了,慌慌张张铲起来就走,我站在旁边眼瞅着箱子掉在地上, “啪嚓”一声砸得我心都直哆嗦。我这嘴是个摆设吗?怎么就不敢吱一声呢。人在矮檐下,天天低着头怕惹事,三十年后,我终于活成了个没用的废物点心,我恨自己。
屋里乱,我收拾完东西到厅里站一会,那边楼道过来两个外班同学跟我打招呼,我也笑脸相对。他俩围着我笑嘻嘻地说:“来看看第一名长什么样!”我心里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并不满意,因此有些哭笑不得。但毕竟比他们高一百多分哪,又不是偷来的,看就看呗,这么一想也就心中坦然了。
同室的嘉骏,是我一生不多的可以称为好朋友的同学,他多年来给了我许多温暧和关怀。1971年11月初中毕业,他作为一名上海知青来到大兴安岭林区。他回忆说:“那时真是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,什么都不知道!”后来他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女子架桥队当电工,吃过不少的苦。农机学院毕业后嘉骏和我一起分配到“北京内燃机总厂”。后来他下海创业,办了个机绣厂,千针几毛钱,挣了些辛苦钱,买了房和车,成了先富起来的人。
另一位上海知青张荣经历更多,他说:“69年上山下乡到大兴安岭塔丰农场,既干过农活,又干过林活,啥活都干,泥瓦匠、造房子、伐木、打枝丫、归楞(抬木头)装车(人工),连森林扑火都干了。我去的时候还是人工伐木,用弯把锯,又累又危险。73年我被推荐在哈尔滨上了两年中专。毕业后又回到大兴安岭瓦拉干储木场当电机技术员,77年考到佳木斯上大学离开了大兴安岭,在大兴安岭里断断续续总共呆了7年,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回到上海,张荣跑到苏州河边买了套公寓,结果歪打正着,苏州河治理后房价陡升。苦尽甜来,他现在常常开车各地漫游,享受着快乐的退休生活。
我对面下铺的显明一直没有音讯,他来自伊春林区的工人家庭。妈妈离婚搬走的时候,他还不懂事,晃着妈妈的手说:“妈,我帮你拔锅去。”后来的日子,父子相依为命,那年父亲一缸腌了三百个咸鸭蛋,没吃完,底下的鸭蛋都成了渣子。父亲终生未再娶,把显明培养成了大学生。显明魁梧英俊,跑、跳、篮球样样都好,二胡拉得更好。他终于和住在四平的妈妈联系上了,我对他说:“让老两口复婚吧。” 显明摇摇头,苦笑道:“妈妈那里又有一大家人了。”同父的漂亮妹妹来看过显明,显明面对着自己的床放了一把椅子,请妹妹坐下,然后对妹妹说:“妹妹,我给你拉二胡听!”于是他坐在床边拉起了名曲《江河水》《病中吟》,悠雅的琴声,浸透长长的思念,这分明是显明对母亲的心声,我听出来了,妹妹也哭了。
班里比我差了快一辈的应届生小同学有好几个,他们也不容易。看到我扒飞车那一段,己华说:“你是夏天,我冬天还这样做过呢,快过年了,火车车厢里人多挤不进去,吊在车外足足40分钟。危险系数比您高一级吧。”接着他回忆了自己这次高考:“回忆我考大学时的情景,两件事印象深刻。一是初试时,在公社小学校。当年农村小学教室生炉子,一般都是每个学生轮流从家里拿柴禾和煤。正值冬天,学校已经放假,没有多余的柴禾,学校临时找点木头,但因潮湿,只冒烟不起火,呛得考生直咳嗽,所以,用雪把炉子沏灭了。而我又坐在靠窗户的位置,不巧的是,玻璃是破的,雪花随风飘到屋里。我一边答题,一边抖落卷子上的雪花,也是醉了。第二件事发生在复试。复试回县城了,在桦南二中。当时家里生活困难,没有手表,我就把家里的马蹄表带来了,放在书桌里。一边苦思冥想答题,一边听着嘀嗒嘀嗒的表声,越答不上来,嘀嗒声越响、越急。好不容易把第一科考完了。从第二科开始就不带表了,因为我觉得监考老师在黑板上画的表挺实用的。”
应了那句后生可畏的话,己华他们几个应届生办事没包袱,又认真仔细,笔杆子也给力,后来发展得最好。我提议办个“班报”,他们几个最积极,写稿、排版、刻蜡板、油印,天天乐得屁颠屁颠的。可惜我存了几十年的“班报”不知收哪儿去了。
大家都鼓励我写下去,张荣留言:“我们都有许多珍贵的回忆。老李写的回忆就很精彩,我看比以前的知青电视剧里的情节要真实,因为那些导演没有经历过,演员也没法感受和体会当年我们的心情。老李完全可以写成回忆录,传世之作,让我们的后代记住知青的一代是怎么回事。”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